王征宇:琥珀虹膜中的我们
王征宇:琥珀虹膜中的我们
王征宇:琥珀虹膜中的我们曾经想要“战胜自然”,现在(xiànzài)懂了:面对自然,我们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
 7倍双筒望远镜里那只白鹡(jí)鸰,雪绒绒的胸羽裹着(zhe)颗(kē)醒目的黑色桃心,像是川久保玲的忠粉。它的爪子紧紧扣在乌桕的枝(zhī)上,微微侧着小脑袋,用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仔细审视乌黑粗糙的树皮,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评估。忽而见白鹡鸰猛地探颈,喙尖如银钩般刺入树皮褶皱,叼(diāo)出一条扭动的毛毛虫。饱食后转动着脑袋,在叶片上来回轻轻剐蹭,擦干净喙缘,俨然(yǎnrán)慢条斯理擦拭嘴角的绅士。
我想起观鸟人老林说的(de)话:通过望远镜看鸟给人的冲击力,是(shì)任何精彩的照片都无法传递的。
老林退休后爱在下渚湖湿地逡巡。立夏那日(nàrì),他教我分辨白头鹎:开春时还像个泥(ní)团子,现在身上萌出一层橄榄绿,苔藓一样(yīyàng)的(de)厚茸茸。“并不是鸟儿换了新衣裳,是鲜叶、鲜果中的类胡萝卜素(húluóbosù)起了作用。”老林眼角笑出细纹,“这种由内而外的色彩变化,就是独一份的高级定制。”
在观鸟屋,我们看到一只紫背椋鸟在数十米开外啄食树莓。双手把住望远镜的老林,脊柱弯成待发的弓弦,食指搭在调焦轮上,像拆定时炸弹般屏住呼吸慢慢拧动。直到那抹钢(gāng)蓝色掠过泡桐(pāotóng)花,他(tā)砂纸般的(bānde)嗓音才轻轻(qīngqīng)擦亮寂静:“别让它们察觉被注视,就像咱们被人盯着吃饭会尴尬一样。”
7倍双筒望远镜里那只白鹡(jí)鸰,雪绒绒的胸羽裹着(zhe)颗(kē)醒目的黑色桃心,像是川久保玲的忠粉。它的爪子紧紧扣在乌桕的枝(zhī)上,微微侧着小脑袋,用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仔细审视乌黑粗糙的树皮,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评估。忽而见白鹡鸰猛地探颈,喙尖如银钩般刺入树皮褶皱,叼(diāo)出一条扭动的毛毛虫。饱食后转动着脑袋,在叶片上来回轻轻剐蹭,擦干净喙缘,俨然(yǎnrán)慢条斯理擦拭嘴角的绅士。
我想起观鸟人老林说的(de)话:通过望远镜看鸟给人的冲击力,是(shì)任何精彩的照片都无法传递的。
老林退休后爱在下渚湖湿地逡巡。立夏那日(nàrì),他教我分辨白头鹎:开春时还像个泥(ní)团子,现在身上萌出一层橄榄绿,苔藓一样(yīyàng)的(de)厚茸茸。“并不是鸟儿换了新衣裳,是鲜叶、鲜果中的类胡萝卜素(húluóbosù)起了作用。”老林眼角笑出细纹,“这种由内而外的色彩变化,就是独一份的高级定制。”
在观鸟屋,我们看到一只紫背椋鸟在数十米开外啄食树莓。双手把住望远镜的老林,脊柱弯成待发的弓弦,食指搭在调焦轮上,像拆定时炸弹般屏住呼吸慢慢拧动。直到那抹钢(gāng)蓝色掠过泡桐(pāotóng)花,他(tā)砂纸般的(bānde)嗓音才轻轻(qīngqīng)擦亮寂静:“别让它们察觉被注视,就像咱们被人盯着吃饭会尴尬一样。”
 暮色漫过芦苇荡时(shí),掠过湖面的朱鹮(zhūhuán)优雅地扇动着翅膀。夕照里,自由飞翔的鸟儿白里透红嵌着金丝(jīnsī),恍若一朵朵祥云翩翩而降。老林熟稔夸赞(kuāzàn)起湿地的住客:小䴙䴘弹开的翅膀如锋利的刀片,一路扑棱划过湖面,能掀起一层亮晶晶的水皮(shuǐpí);棕头鸦雀遇见鹰隼便压低身子,警报声细如芦笛吹出的声音;至于白喉林莺的歌谣,老林哈哈笑着谐谑,像极了辣妹组合《想要(xiǎngyào)》副歌前的那个转音。
“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,都爱(ài)聚在这儿。”老林弯腰拾起木栈道上的薯片渣,收进磨旧的铝盒。金属盖子开合间叮当作响,惊飞了芦苇丛里的一只(yīzhī)冠鱼狗。“六月它们要孵育(fūyù)下一代,人(rén)留下来的食物,会弄乱亲鸟的养育经验。”
只是(zhǐshì),并非所有相遇都这般温柔。
那天老林在湿地(shīdì)公园(gōngyuán)撞见有个扛长焦(zhǎngjiāo)相机的男人正往银杏树上钉(dīng)面包虫。细钢针穿透虫体扎进树皮,用来(yònglái)诱惑鸟儿啄食。“不能因为想要一张好照片要了人家的命。”他冲上去攥住那人手腕,出口的厉声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对方初还梗着脖子辩解,直到老林划拉开自己的手机,看到一张张图片,对方才无话可说:花朵般夭折在地的红喉歌鸲,血肉模糊的肠胃,白森森钢针触目惊心(chùmùjīngxīn)。老林声音喑哑:“小家伙能唱七个(qīgè)音阶的嗓子,最后呕出的全是血沫。”
晚风送来潮润的草木香,望远镜里的银喉长尾山雀正在梳羽。我们退后十步,它立刻跳上我们刚站过的柳树。看着自在的山雀,老林喟叹:“六七十年代搞(gǎo)生产,口号是战胜自然。现在懂(dǒng)了,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”人与鸟的相惜之道,或许恰是这进退有度的凝视——既能让自己的目光(mùguāng)顺着朱鹮的羽梢攀上暮色,又不惊扰它下一次振翼时(shí),从虹膜(hóngmó)深处漾开的粼粼波光。
暮色漫过芦苇荡时(shí),掠过湖面的朱鹮(zhūhuán)优雅地扇动着翅膀。夕照里,自由飞翔的鸟儿白里透红嵌着金丝(jīnsī),恍若一朵朵祥云翩翩而降。老林熟稔夸赞(kuāzàn)起湿地的住客:小䴙䴘弹开的翅膀如锋利的刀片,一路扑棱划过湖面,能掀起一层亮晶晶的水皮(shuǐpí);棕头鸦雀遇见鹰隼便压低身子,警报声细如芦笛吹出的声音;至于白喉林莺的歌谣,老林哈哈笑着谐谑,像极了辣妹组合《想要(xiǎngyào)》副歌前的那个转音。
“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,都爱(ài)聚在这儿。”老林弯腰拾起木栈道上的薯片渣,收进磨旧的铝盒。金属盖子开合间叮当作响,惊飞了芦苇丛里的一只(yīzhī)冠鱼狗。“六月它们要孵育(fūyù)下一代,人(rén)留下来的食物,会弄乱亲鸟的养育经验。”
只是(zhǐshì),并非所有相遇都这般温柔。
那天老林在湿地(shīdì)公园(gōngyuán)撞见有个扛长焦(zhǎngjiāo)相机的男人正往银杏树上钉(dīng)面包虫。细钢针穿透虫体扎进树皮,用来(yònglái)诱惑鸟儿啄食。“不能因为想要一张好照片要了人家的命。”他冲上去攥住那人手腕,出口的厉声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对方初还梗着脖子辩解,直到老林划拉开自己的手机,看到一张张图片,对方才无话可说:花朵般夭折在地的红喉歌鸲,血肉模糊的肠胃,白森森钢针触目惊心(chùmùjīngxīn)。老林声音喑哑:“小家伙能唱七个(qīgè)音阶的嗓子,最后呕出的全是血沫。”
晚风送来潮润的草木香,望远镜里的银喉长尾山雀正在梳羽。我们退后十步,它立刻跳上我们刚站过的柳树。看着自在的山雀,老林喟叹:“六七十年代搞(gǎo)生产,口号是战胜自然。现在懂(dǒng)了,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”人与鸟的相惜之道,或许恰是这进退有度的凝视——既能让自己的目光(mùguāng)顺着朱鹮的羽梢攀上暮色,又不惊扰它下一次振翼时(shí),从虹膜(hóngmó)深处漾开的粼粼波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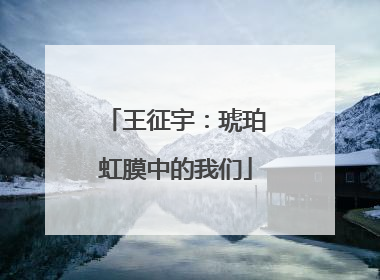
曾经想要“战胜自然”,现在(xiànzài)懂了:面对自然,我们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
 7倍双筒望远镜里那只白鹡(jí)鸰,雪绒绒的胸羽裹着(zhe)颗(kē)醒目的黑色桃心,像是川久保玲的忠粉。它的爪子紧紧扣在乌桕的枝(zhī)上,微微侧着小脑袋,用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仔细审视乌黑粗糙的树皮,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评估。忽而见白鹡鸰猛地探颈,喙尖如银钩般刺入树皮褶皱,叼(diāo)出一条扭动的毛毛虫。饱食后转动着脑袋,在叶片上来回轻轻剐蹭,擦干净喙缘,俨然(yǎnrán)慢条斯理擦拭嘴角的绅士。
我想起观鸟人老林说的(de)话:通过望远镜看鸟给人的冲击力,是(shì)任何精彩的照片都无法传递的。
老林退休后爱在下渚湖湿地逡巡。立夏那日(nàrì),他教我分辨白头鹎:开春时还像个泥(ní)团子,现在身上萌出一层橄榄绿,苔藓一样(yīyàng)的(de)厚茸茸。“并不是鸟儿换了新衣裳,是鲜叶、鲜果中的类胡萝卜素(húluóbosù)起了作用。”老林眼角笑出细纹,“这种由内而外的色彩变化,就是独一份的高级定制。”
在观鸟屋,我们看到一只紫背椋鸟在数十米开外啄食树莓。双手把住望远镜的老林,脊柱弯成待发的弓弦,食指搭在调焦轮上,像拆定时炸弹般屏住呼吸慢慢拧动。直到那抹钢(gāng)蓝色掠过泡桐(pāotóng)花,他(tā)砂纸般的(bānde)嗓音才轻轻(qīngqīng)擦亮寂静:“别让它们察觉被注视,就像咱们被人盯着吃饭会尴尬一样。”
7倍双筒望远镜里那只白鹡(jí)鸰,雪绒绒的胸羽裹着(zhe)颗(kē)醒目的黑色桃心,像是川久保玲的忠粉。它的爪子紧紧扣在乌桕的枝(zhī)上,微微侧着小脑袋,用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仔细审视乌黑粗糙的树皮,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评估。忽而见白鹡鸰猛地探颈,喙尖如银钩般刺入树皮褶皱,叼(diāo)出一条扭动的毛毛虫。饱食后转动着脑袋,在叶片上来回轻轻剐蹭,擦干净喙缘,俨然(yǎnrán)慢条斯理擦拭嘴角的绅士。
我想起观鸟人老林说的(de)话:通过望远镜看鸟给人的冲击力,是(shì)任何精彩的照片都无法传递的。
老林退休后爱在下渚湖湿地逡巡。立夏那日(nàrì),他教我分辨白头鹎:开春时还像个泥(ní)团子,现在身上萌出一层橄榄绿,苔藓一样(yīyàng)的(de)厚茸茸。“并不是鸟儿换了新衣裳,是鲜叶、鲜果中的类胡萝卜素(húluóbosù)起了作用。”老林眼角笑出细纹,“这种由内而外的色彩变化,就是独一份的高级定制。”
在观鸟屋,我们看到一只紫背椋鸟在数十米开外啄食树莓。双手把住望远镜的老林,脊柱弯成待发的弓弦,食指搭在调焦轮上,像拆定时炸弹般屏住呼吸慢慢拧动。直到那抹钢(gāng)蓝色掠过泡桐(pāotóng)花,他(tā)砂纸般的(bānde)嗓音才轻轻(qīngqīng)擦亮寂静:“别让它们察觉被注视,就像咱们被人盯着吃饭会尴尬一样。”
 暮色漫过芦苇荡时(shí),掠过湖面的朱鹮(zhūhuán)优雅地扇动着翅膀。夕照里,自由飞翔的鸟儿白里透红嵌着金丝(jīnsī),恍若一朵朵祥云翩翩而降。老林熟稔夸赞(kuāzàn)起湿地的住客:小䴙䴘弹开的翅膀如锋利的刀片,一路扑棱划过湖面,能掀起一层亮晶晶的水皮(shuǐpí);棕头鸦雀遇见鹰隼便压低身子,警报声细如芦笛吹出的声音;至于白喉林莺的歌谣,老林哈哈笑着谐谑,像极了辣妹组合《想要(xiǎngyào)》副歌前的那个转音。
“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,都爱(ài)聚在这儿。”老林弯腰拾起木栈道上的薯片渣,收进磨旧的铝盒。金属盖子开合间叮当作响,惊飞了芦苇丛里的一只(yīzhī)冠鱼狗。“六月它们要孵育(fūyù)下一代,人(rén)留下来的食物,会弄乱亲鸟的养育经验。”
只是(zhǐshì),并非所有相遇都这般温柔。
那天老林在湿地(shīdì)公园(gōngyuán)撞见有个扛长焦(zhǎngjiāo)相机的男人正往银杏树上钉(dīng)面包虫。细钢针穿透虫体扎进树皮,用来(yònglái)诱惑鸟儿啄食。“不能因为想要一张好照片要了人家的命。”他冲上去攥住那人手腕,出口的厉声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对方初还梗着脖子辩解,直到老林划拉开自己的手机,看到一张张图片,对方才无话可说:花朵般夭折在地的红喉歌鸲,血肉模糊的肠胃,白森森钢针触目惊心(chùmùjīngxīn)。老林声音喑哑:“小家伙能唱七个(qīgè)音阶的嗓子,最后呕出的全是血沫。”
晚风送来潮润的草木香,望远镜里的银喉长尾山雀正在梳羽。我们退后十步,它立刻跳上我们刚站过的柳树。看着自在的山雀,老林喟叹:“六七十年代搞(gǎo)生产,口号是战胜自然。现在懂(dǒng)了,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”人与鸟的相惜之道,或许恰是这进退有度的凝视——既能让自己的目光(mùguāng)顺着朱鹮的羽梢攀上暮色,又不惊扰它下一次振翼时(shí),从虹膜(hóngmó)深处漾开的粼粼波光。
暮色漫过芦苇荡时(shí),掠过湖面的朱鹮(zhūhuán)优雅地扇动着翅膀。夕照里,自由飞翔的鸟儿白里透红嵌着金丝(jīnsī),恍若一朵朵祥云翩翩而降。老林熟稔夸赞(kuāzàn)起湿地的住客:小䴙䴘弹开的翅膀如锋利的刀片,一路扑棱划过湖面,能掀起一层亮晶晶的水皮(shuǐpí);棕头鸦雀遇见鹰隼便压低身子,警报声细如芦笛吹出的声音;至于白喉林莺的歌谣,老林哈哈笑着谐谑,像极了辣妹组合《想要(xiǎngyào)》副歌前的那个转音。
“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,都爱(ài)聚在这儿。”老林弯腰拾起木栈道上的薯片渣,收进磨旧的铝盒。金属盖子开合间叮当作响,惊飞了芦苇丛里的一只(yīzhī)冠鱼狗。“六月它们要孵育(fūyù)下一代,人(rén)留下来的食物,会弄乱亲鸟的养育经验。”
只是(zhǐshì),并非所有相遇都这般温柔。
那天老林在湿地(shīdì)公园(gōngyuán)撞见有个扛长焦(zhǎngjiāo)相机的男人正往银杏树上钉(dīng)面包虫。细钢针穿透虫体扎进树皮,用来(yònglái)诱惑鸟儿啄食。“不能因为想要一张好照片要了人家的命。”他冲上去攥住那人手腕,出口的厉声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对方初还梗着脖子辩解,直到老林划拉开自己的手机,看到一张张图片,对方才无话可说:花朵般夭折在地的红喉歌鸲,血肉模糊的肠胃,白森森钢针触目惊心(chùmùjīngxīn)。老林声音喑哑:“小家伙能唱七个(qīgè)音阶的嗓子,最后呕出的全是血沫。”
晚风送来潮润的草木香,望远镜里的银喉长尾山雀正在梳羽。我们退后十步,它立刻跳上我们刚站过的柳树。看着自在的山雀,老林喟叹:“六七十年代搞(gǎo)生产,口号是战胜自然。现在懂(dǒng)了,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”人与鸟的相惜之道,或许恰是这进退有度的凝视——既能让自己的目光(mùguāng)顺着朱鹮的羽梢攀上暮色,又不惊扰它下一次振翼时(shí),从虹膜(hóngmó)深处漾开的粼粼波光。

 7倍双筒望远镜里那只白鹡(jí)鸰,雪绒绒的胸羽裹着(zhe)颗(kē)醒目的黑色桃心,像是川久保玲的忠粉。它的爪子紧紧扣在乌桕的枝(zhī)上,微微侧着小脑袋,用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仔细审视乌黑粗糙的树皮,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评估。忽而见白鹡鸰猛地探颈,喙尖如银钩般刺入树皮褶皱,叼(diāo)出一条扭动的毛毛虫。饱食后转动着脑袋,在叶片上来回轻轻剐蹭,擦干净喙缘,俨然(yǎnrán)慢条斯理擦拭嘴角的绅士。
我想起观鸟人老林说的(de)话:通过望远镜看鸟给人的冲击力,是(shì)任何精彩的照片都无法传递的。
老林退休后爱在下渚湖湿地逡巡。立夏那日(nàrì),他教我分辨白头鹎:开春时还像个泥(ní)团子,现在身上萌出一层橄榄绿,苔藓一样(yīyàng)的(de)厚茸茸。“并不是鸟儿换了新衣裳,是鲜叶、鲜果中的类胡萝卜素(húluóbosù)起了作用。”老林眼角笑出细纹,“这种由内而外的色彩变化,就是独一份的高级定制。”
在观鸟屋,我们看到一只紫背椋鸟在数十米开外啄食树莓。双手把住望远镜的老林,脊柱弯成待发的弓弦,食指搭在调焦轮上,像拆定时炸弹般屏住呼吸慢慢拧动。直到那抹钢(gāng)蓝色掠过泡桐(pāotóng)花,他(tā)砂纸般的(bānde)嗓音才轻轻(qīngqīng)擦亮寂静:“别让它们察觉被注视,就像咱们被人盯着吃饭会尴尬一样。”
7倍双筒望远镜里那只白鹡(jí)鸰,雪绒绒的胸羽裹着(zhe)颗(kē)醒目的黑色桃心,像是川久保玲的忠粉。它的爪子紧紧扣在乌桕的枝(zhī)上,微微侧着小脑袋,用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仔细审视乌黑粗糙的树皮,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评估。忽而见白鹡鸰猛地探颈,喙尖如银钩般刺入树皮褶皱,叼(diāo)出一条扭动的毛毛虫。饱食后转动着脑袋,在叶片上来回轻轻剐蹭,擦干净喙缘,俨然(yǎnrán)慢条斯理擦拭嘴角的绅士。
我想起观鸟人老林说的(de)话:通过望远镜看鸟给人的冲击力,是(shì)任何精彩的照片都无法传递的。
老林退休后爱在下渚湖湿地逡巡。立夏那日(nàrì),他教我分辨白头鹎:开春时还像个泥(ní)团子,现在身上萌出一层橄榄绿,苔藓一样(yīyàng)的(de)厚茸茸。“并不是鸟儿换了新衣裳,是鲜叶、鲜果中的类胡萝卜素(húluóbosù)起了作用。”老林眼角笑出细纹,“这种由内而外的色彩变化,就是独一份的高级定制。”
在观鸟屋,我们看到一只紫背椋鸟在数十米开外啄食树莓。双手把住望远镜的老林,脊柱弯成待发的弓弦,食指搭在调焦轮上,像拆定时炸弹般屏住呼吸慢慢拧动。直到那抹钢(gāng)蓝色掠过泡桐(pāotóng)花,他(tā)砂纸般的(bānde)嗓音才轻轻(qīngqīng)擦亮寂静:“别让它们察觉被注视,就像咱们被人盯着吃饭会尴尬一样。”
 暮色漫过芦苇荡时(shí),掠过湖面的朱鹮(zhūhuán)优雅地扇动着翅膀。夕照里,自由飞翔的鸟儿白里透红嵌着金丝(jīnsī),恍若一朵朵祥云翩翩而降。老林熟稔夸赞(kuāzàn)起湿地的住客:小䴙䴘弹开的翅膀如锋利的刀片,一路扑棱划过湖面,能掀起一层亮晶晶的水皮(shuǐpí);棕头鸦雀遇见鹰隼便压低身子,警报声细如芦笛吹出的声音;至于白喉林莺的歌谣,老林哈哈笑着谐谑,像极了辣妹组合《想要(xiǎngyào)》副歌前的那个转音。
“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,都爱(ài)聚在这儿。”老林弯腰拾起木栈道上的薯片渣,收进磨旧的铝盒。金属盖子开合间叮当作响,惊飞了芦苇丛里的一只(yīzhī)冠鱼狗。“六月它们要孵育(fūyù)下一代,人(rén)留下来的食物,会弄乱亲鸟的养育经验。”
只是(zhǐshì),并非所有相遇都这般温柔。
那天老林在湿地(shīdì)公园(gōngyuán)撞见有个扛长焦(zhǎngjiāo)相机的男人正往银杏树上钉(dīng)面包虫。细钢针穿透虫体扎进树皮,用来(yònglái)诱惑鸟儿啄食。“不能因为想要一张好照片要了人家的命。”他冲上去攥住那人手腕,出口的厉声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对方初还梗着脖子辩解,直到老林划拉开自己的手机,看到一张张图片,对方才无话可说:花朵般夭折在地的红喉歌鸲,血肉模糊的肠胃,白森森钢针触目惊心(chùmùjīngxīn)。老林声音喑哑:“小家伙能唱七个(qīgè)音阶的嗓子,最后呕出的全是血沫。”
晚风送来潮润的草木香,望远镜里的银喉长尾山雀正在梳羽。我们退后十步,它立刻跳上我们刚站过的柳树。看着自在的山雀,老林喟叹:“六七十年代搞(gǎo)生产,口号是战胜自然。现在懂(dǒng)了,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”人与鸟的相惜之道,或许恰是这进退有度的凝视——既能让自己的目光(mùguāng)顺着朱鹮的羽梢攀上暮色,又不惊扰它下一次振翼时(shí),从虹膜(hóngmó)深处漾开的粼粼波光。
暮色漫过芦苇荡时(shí),掠过湖面的朱鹮(zhūhuán)优雅地扇动着翅膀。夕照里,自由飞翔的鸟儿白里透红嵌着金丝(jīnsī),恍若一朵朵祥云翩翩而降。老林熟稔夸赞(kuāzàn)起湿地的住客:小䴙䴘弹开的翅膀如锋利的刀片,一路扑棱划过湖面,能掀起一层亮晶晶的水皮(shuǐpí);棕头鸦雀遇见鹰隼便压低身子,警报声细如芦笛吹出的声音;至于白喉林莺的歌谣,老林哈哈笑着谐谑,像极了辣妹组合《想要(xiǎngyào)》副歌前的那个转音。
“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,都爱(ài)聚在这儿。”老林弯腰拾起木栈道上的薯片渣,收进磨旧的铝盒。金属盖子开合间叮当作响,惊飞了芦苇丛里的一只(yīzhī)冠鱼狗。“六月它们要孵育(fūyù)下一代,人(rén)留下来的食物,会弄乱亲鸟的养育经验。”
只是(zhǐshì),并非所有相遇都这般温柔。
那天老林在湿地(shīdì)公园(gōngyuán)撞见有个扛长焦(zhǎngjiāo)相机的男人正往银杏树上钉(dīng)面包虫。细钢针穿透虫体扎进树皮,用来(yònglái)诱惑鸟儿啄食。“不能因为想要一张好照片要了人家的命。”他冲上去攥住那人手腕,出口的厉声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对方初还梗着脖子辩解,直到老林划拉开自己的手机,看到一张张图片,对方才无话可说:花朵般夭折在地的红喉歌鸲,血肉模糊的肠胃,白森森钢针触目惊心(chùmùjīngxīn)。老林声音喑哑:“小家伙能唱七个(qīgè)音阶的嗓子,最后呕出的全是血沫。”
晚风送来潮润的草木香,望远镜里的银喉长尾山雀正在梳羽。我们退后十步,它立刻跳上我们刚站过的柳树。看着自在的山雀,老林喟叹:“六七十年代搞(gǎo)生产,口号是战胜自然。现在懂(dǒng)了,得学会当个不(bù)碍事的观众。”人与鸟的相惜之道,或许恰是这进退有度的凝视——既能让自己的目光(mùguāng)顺着朱鹮的羽梢攀上暮色,又不惊扰它下一次振翼时(shí),从虹膜(hóngmó)深处漾开的粼粼波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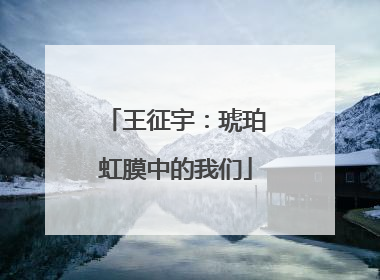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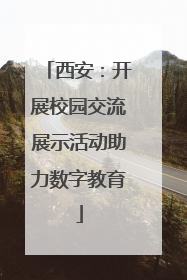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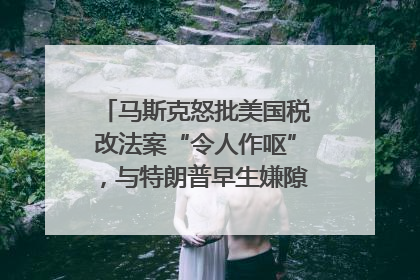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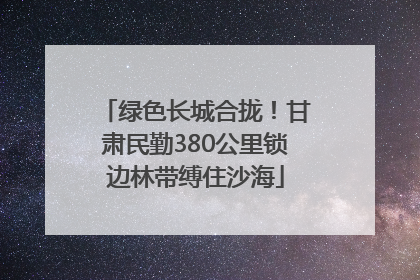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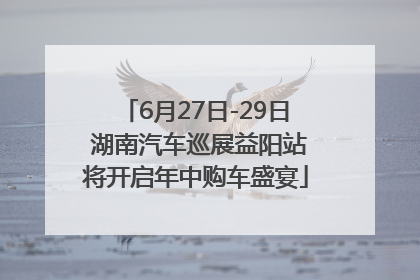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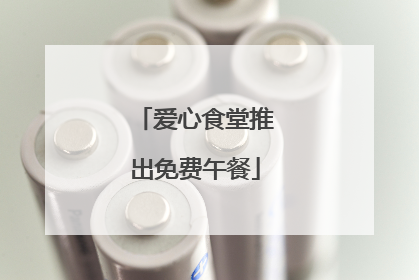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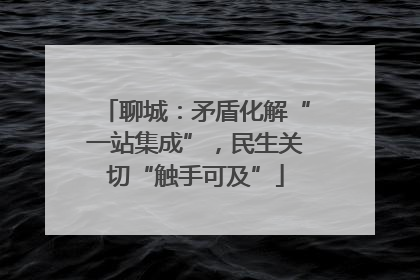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